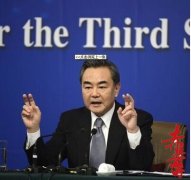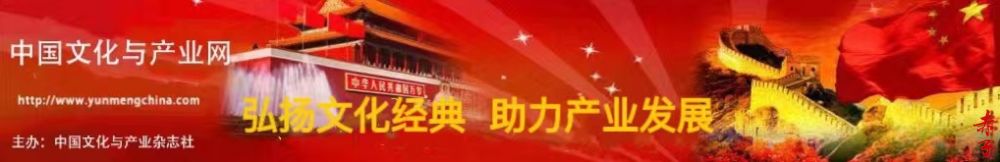

公共危机事件中政府、媒体和公众角色定位研究 ——基于“8.12天津滨海新区爆炸事故”的个案分析
来源: 发布时间:2017-12-06
浏览次数: 8339
公共危机事件中政府、媒体和公众角色定位研究
——基于“8.12天津滨海新区爆炸事故”的个案分析
作者:卞琰 指导老师:孙璐
摘要:在不断变革的社会中,公共危机事件发生概率增大,本文以天津滨海新区爆炸事故为分析对象,剖析政府、媒体、公众在此次事件中的角色作用。进而进一步分析公共危机事件的酝酿期、爆发期、扩散期、处理期、处理结果和后遗症期中三者的应然角色,政府做好预警者、解决者、安抚者,媒体扮演好协力者、宣传者、安全阀角色,公众配合、监督政府工作,形成良性的沟通互动关系才能较好地处理此类事件需要,降低公共危机事件的破坏力。
关键词:角色研究,政府,媒体,公众,公共危机事件
一、引言
在经验的层面上,一个广为人知并接受的论断是,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以后,社会既进入黄金发展期,也进入风险高发期。[1]显然现在的中国已经进入风险社会,公共危机事件难以避免,又因其突发性、演变不确定性,群体扩散性等特点,有别于一般的突发事件。[2]如果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的杀伤力相较于事件本身,有过之而无不及。政府、媒体、公众在此类危机事件的处理中都起着重要作用,根据斯蒂芬·芬克的危机生命周期理论,危机存在酝酿期、爆发期、扩散期、处理期、处理结果和后遗症期[3],三者角色存在差异,其中这类事件中危机酝酿期除政府外其他主体的作用微小。政府不同的处理方式、媒体不同的报道内容与方式都会对公众的行为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
二、案例导入
2015年8月12日晚11时30分,天津滨海新区瑞海公司所属危险品仓库发生爆炸,随后发生二次爆炸。爆炸发生后的第一时间,当地网民就在微博和微信上发布相关消息及视频。公众此时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就是事件的传播者,替代了媒体在此时的角色,主要原因是新媒体的发展,人人手握“麦克风”。此时的天津卫视在播放韩剧,反映及时的几家媒体也是在13日凌晨介入报道,可以看出主流媒体没有能够及时发挥自己传递信息的作用。
另一方面,在事件的扩散期和处理期,当地政府很快召开新闻发布会,前六次(8月16日前)效果不佳,发布会上的相关言论不仅没有向公众解释清楚事件的来龙去脉,对公众关注的消防救援措施问题、爆炸原因、环境监测及伤亡数据均不能提供满意答复,成为民间舆论的新导火索。实际上,我国新闻媒体“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的双重属性,使其具有政府喉舌与市场主体的双重角色身份。这种身份促使媒体在公共危机报道中形成了既服从政府统一报道口径的安排, 又寻求自由报道空间来赢得市场的“中间角色”。[4]而在“8.12”事件中前六次的发布会直播中断,媒体提问环节直接不公开,引发了一场舆论危机。公众的反应不断推动媒体的报道与政府的回应速度与回应可信性进程。
爆炸案发生两个月后,媒体密切关注事件处理的坚持,表示“唯有追问才能真相大白”。李克强总理也曾在9月21日天津大爆炸事件进展回报上做出“血不能白流、代价不能白付,要将问责进行到底。”的表态。检查专案调查组对在审批、管理和监督等环节存在严重失职渎职问题的相关负责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移交法院依法处理。对当地居民的安抚处理、安居修缮处理此时接近尾声,但将灾后地规划建设“海港生态公园”,被媒体、公众质疑有可能造成二次污染,治标不治本。另外,据中国之声报道,事件发生的二十天内当地收到不少捐款,天津市社会团体管理局及时公示了信息,这些捐赠款物的使用也做到了信息公开。
三、公共危机事件中政府、媒体、公众角色研究
(一)政府角色
首先要明确的是在公共危机沟通的价值取向,应将信息公开确立为公共危机沟通的基本价值取向,将以人为本确立为公共危机沟通的核心价值取向,将社会和谐确立为公共危机沟通的终极价值取向。[5]
在公共危机事件的酝酿期需要政府尽到应急预警机制的制定者的职责,作为公共政策的制定主体之一、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完善政府预警机制能够有效应对突发危机事件,甚至降低危机事件发生的概率。并且《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五条中明确规定:“突发事件应对工作实行预防为主、预防与应急相结合的原则。”。在“8.12”这类突发性危机事件的酝酿期不明显,但我认为政府的预防者的角色还是应当发挥其作用,定期排查安全隐患,尤其是对危险品的存放制定更为严格的要求,或者对当前风险情况进行细致、周全、负责的评估,避免概论疏忽、结果疏忽、统计疏忽、应对方案疏忽、外部风险疏忽,[6]例如汶川地震之前如果能更好地宣传四川处于活动断层的地震知识,可能提高当地建筑标准,可以很大程度上降低此类事件的发生或减少其损害后果。
我国的预警机制不健全主要体现在缺乏足够的灾害应急准备。对危机管理而言,获取信息、相互协调、沟通的基础条件就是对突发事件实行实时监控。2013年的四川雅安地震、2014年的云南景谷地震,我国的地震预警都没有发挥好作用,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7]
到了危机事件的爆发期、扩散期和处理期,政府应当充当危机事件的解决者,由于政府的特殊地位,拥有着强大的组织协调和干预能力,以及无与伦比的社会资源,使得政府在公共危机处理过程中占据绝对的主体地位,发挥着主导作用,应当履行好社会管理职能。其中,在爆发初期及时做出反应至关重要,决定了危机事件的走向。在危机处理阶段,政府要做的绝不是尽快开新闻发布,因为前期调查还没有结束,事故发生原因尚未明晰,这个时候的政府很难给出令人满意的答复。政府需要明白此时应该先做好解决者的本分工作,随后及时公开处理情况,而不是同“8.12”事件中使用“无可奉告”之类的托辞。
危机事件发展到最后的处理结果和后遗症期时,政府应当做好危机事件的总结工作和公众的情绪安抚。政府内部的总结不止于如何做好危机的收尾工作,还要找出事件发生时处理不当的地方以及如何完善,总结该次危机应对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健全危机应对机制,对危机尚存缺陷的方面进行及时弥补和更新,强化各层级官员的行政责任意识。
突发危机事件处理不当很有可能出现政府信任受损的后遗症,当政府信任受损之后,社会公众可能终止与政府积极的互动(如合作、执行政府的政策等),甚至产生消极的互动(如反面预期、游行、示威等),公众不会配合、甚至抵制政府的公共政策,且这种情况可能一直持续到政府采取有效的修复措施。这些负面行为对政府的公共管理产生挑战,因此必须采取措施将政府信任调整回积极的状态。[8]
(二)媒体角色
1948年,美国社会学家、传播学先驱哈罗德·拉斯韦尔在《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中归纳了传媒的三种社会功能,即“环境监视功能”、“社会协调功能”和“社会遗产传承功能”。传媒作为政府和公众之间的桥梁,在公共危机事件的四个时期都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并且新媒体的迅速发展让媒体的发声渠道更加多元化,影响力也在攀升。
由于公共危机事件酝酿期基本不存在,媒体在其他公共危机事件中的敏锐预警者作用难以发挥。在爆发期,这时候的媒体需要发挥作为公众知情权捍卫者和公共危机管理协力者的作用。由于爆发初期,信息的不对称让公众很容易陷入恐慌之中,知情权亟需保障。媒体可以将公共危机信息直接传递给公众,减少信息传递环节,避免信息失真的概率,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谣言和小道消息的产生或终止谣言和小道消息的传播,帮助政府传递信息,协助政府进行公共危机预防、反应和恢复。[9]在2011年温州“抢盐”风波中《温州日报》及时发现并且运用大幅版面报道众生百态,也组织发布击碎“谣盐”的专家文章,充分发挥了协力者作用。
当事件发展到扩散期时,媒体一方面充当政府政策的宣传者,既然危机事件已经产生广泛影响,那么媒体就需要宣传政府有关部门的应急措施,给公众打一剂强心针,为后续事件解决打好基础。另一方面,媒体还需要成为舆情的收集传递者,政府的信息在经过层级传递后,难免发生信息失真、滞后的情况,而处在第一线的媒体能够直观地还原现实。最后的处理期和处理结果和后遗症期,媒体则要推动真相的还原,不断更新危机事件的最新状态,同时能够究其根源,让政府和公众都能从危机事件中汲取经验教训,而不是只在风口浪尖上集中报道,要充分发挥媒体的监督功能。
在后四个时期媒体还有一个共同的角色定位——排气孔和安全阀。媒体关于突发性危机事件中正面或负面的报道都可以排解公众或消极或愤懑或悲伤的情绪,不至于让社会负面情绪的挤压威胁社会稳定,媒体应当成为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所言的社会的“安全阀”。
(三)公众角色
绝大部分公众是不能预知到公共危机事件的,尤其是突发性公共危机时间内,公众能做的就是在危机事件未发生时做好应急知识的学习者,对政府制定的应急方案有一定的了解,汲取媒体传播的预警防护知识,提高自我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参与仿真演练。
在社会面临突发性重大危机时,人的首要需求应是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这两个较低层次的需求。人们一般更喜欢一个安全、可以预料、有组织、有纪律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他所可以依赖的,甚至认为几乎一切都不如安全需要。[10]那么,公众在危机事件爆发时,意识到自己的生命、生存环境受到威胁时,自然就会变成迫切需要信息的接受者,强烈对信息的需求促使公众从最初的不知所措心理恐慌为参与到积极信息传播过程中,尤其是在前四个时期,公众渴望从各种渠道获得信息,追求确定性,同时也不自觉地成为危机信息的传播者,比如“8.12”事件中公众是最早传播相关情况的主体。另一方面,自媒体受众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信息,同时通过媒介发表自己的看法,反馈的速度快到甚至能打乱拉斯韦尔的“5W”传播过程模式。
公共危机事件进入扩散期时,公众就转变成参与者和推动者,一旦事件影响蔓延开来,公众对主体部门应对措施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事件能否尽快解决。在“8.12”事件中公众通过微博、微信平台表达自己的诉求与观点,对政府的回应表示不满反过来迫使政府提供有效信息。这也是公众的权利意识加强,社会参与感提高的表现。
最后的处理期和处理结果和后遗症期,公众更多的是以评价监督者的角色出现。公众作为事件的参与者,他们的意见和评价自然很有价值,通过媒体进行汇总,形成舆情,为政府完善公共危机事件应对策略提供参考。同时,公众能够直观看到事件的后续处理,监督权也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发挥好监督的权利也能促进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
四、政府、媒体、公众互动关系构建
为了能够在实际中更好地扮演各自的角色,政府、媒体和公众应当保持良好的互动、沟通关系。政府与媒体间既相互联系、影响。在危机事件的任何时期,政府都需要媒体为其传递相关讯息,无论预警机制的宣传还是危机信息发布及舆论引导都离不开媒体。这也是“8.12”事件中相关部门紧急召开发布会的原因。也就是说,媒体能够对政府能否尽快解决公共危机事件、是否将危机对社会、公众的影响降到最低起着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在公共危机事件上媒体是否能够及时报道相关信息(从政府方面获取)以及如何报道对其塑造自身形象也有很大影响。当然,媒体对政府还有监督的作用,对于“8.12”事件的处理方式及后续结果,媒体都是密切关注的,并且呼吁对类似的危险品储存严格审查。
就公众层面来讲,与媒体存在着代理关系;对媒体而言,与公众有着信息交换关系。虽然自媒体时代公众也可以发挥媒体的一部分作用,但是主流媒体的影响力远超个人,公众需要媒体的发声。另一方面,政府与公众存在着监督与被监督关系以及合作关系。“众人拾柴火焰高”,光凭政府处理危机事件的效率有限,在专业性要求不高的工作上,公众的参与能够加快危机事件的解决速度。同时,公众也能更好地监督政府工作,减少谣言的产生。
总之,在公共危机事件的酝酿时期政府能够做好预警者,媒体能够为政府的相关政策措施进行宣传,公众能够认真学习;爆发期、扩散期政府能够及时妥善处理,媒体能够在宣传政府解决方案时传递公众的意见,监督政府工作,给公众发泄的渠道,公众理性发声,帮助政府解决问题;处理期和后遗症政府与媒体及时公布进程,做好安抚工作,尽快恢复公众对其的信任,媒体与公众监督政府工作同时给出评价,以便政府总结工作经验与不足。
参考文献:
[1]张海波,童星.中国应急管理结构变化及其理论概化[J].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03期:62.
[2]丁迈,罗佳.心理应激影响下公共危机事件的公众舆论流变——以“昆明暴恐”事件为例[J].现代传播,2015年第2期:50.
[3]斯蒂芬·芬克.危机管理[M].湖南:湖南文艺出版社,2008.
[4]周榕,张德胜.论我国媒体在公共危机事件中的“中间角色”[J].传媒观察,2014年05期:20.
[5]陈世瑞.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沟通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91-94.
[6]霍华德·昆鲁斯,迈克尔·尤西姆等.灾难的启示:建立有效的应急反应战略[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6:75-85.
[7]申振东,郭勇,张罗娜.关于我国公共危机管理的思考——基于近三年60起典型突发事件的分析[J].贵州社会科学,2016年6月第6期:73.
[8]徐彪.公共危机事件后的政府信任修复[J].中国行政管理,2013年第2期:32.
[9]叶春涛.突发公共危机事件处置中地方政府与媒体的角色扮演[J].社科纵横,2013年11期:62.
[10]马斯洛.动机与人格[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基于“8.12天津滨海新区爆炸事故”的个案分析
作者:卞琰 指导老师:孙璐
摘要:在不断变革的社会中,公共危机事件发生概率增大,本文以天津滨海新区爆炸事故为分析对象,剖析政府、媒体、公众在此次事件中的角色作用。进而进一步分析公共危机事件的酝酿期、爆发期、扩散期、处理期、处理结果和后遗症期中三者的应然角色,政府做好预警者、解决者、安抚者,媒体扮演好协力者、宣传者、安全阀角色,公众配合、监督政府工作,形成良性的沟通互动关系才能较好地处理此类事件需要,降低公共危机事件的破坏力。
关键词:角色研究,政府,媒体,公众,公共危机事件
一、引言
在经验的层面上,一个广为人知并接受的论断是,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以后,社会既进入黄金发展期,也进入风险高发期。[1]显然现在的中国已经进入风险社会,公共危机事件难以避免,又因其突发性、演变不确定性,群体扩散性等特点,有别于一般的突发事件。[2]如果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的杀伤力相较于事件本身,有过之而无不及。政府、媒体、公众在此类危机事件的处理中都起着重要作用,根据斯蒂芬·芬克的危机生命周期理论,危机存在酝酿期、爆发期、扩散期、处理期、处理结果和后遗症期[3],三者角色存在差异,其中这类事件中危机酝酿期除政府外其他主体的作用微小。政府不同的处理方式、媒体不同的报道内容与方式都会对公众的行为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
二、案例导入
2015年8月12日晚11时30分,天津滨海新区瑞海公司所属危险品仓库发生爆炸,随后发生二次爆炸。爆炸发生后的第一时间,当地网民就在微博和微信上发布相关消息及视频。公众此时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就是事件的传播者,替代了媒体在此时的角色,主要原因是新媒体的发展,人人手握“麦克风”。此时的天津卫视在播放韩剧,反映及时的几家媒体也是在13日凌晨介入报道,可以看出主流媒体没有能够及时发挥自己传递信息的作用。
另一方面,在事件的扩散期和处理期,当地政府很快召开新闻发布会,前六次(8月16日前)效果不佳,发布会上的相关言论不仅没有向公众解释清楚事件的来龙去脉,对公众关注的消防救援措施问题、爆炸原因、环境监测及伤亡数据均不能提供满意答复,成为民间舆论的新导火索。实际上,我国新闻媒体“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的双重属性,使其具有政府喉舌与市场主体的双重角色身份。这种身份促使媒体在公共危机报道中形成了既服从政府统一报道口径的安排, 又寻求自由报道空间来赢得市场的“中间角色”。[4]而在“8.12”事件中前六次的发布会直播中断,媒体提问环节直接不公开,引发了一场舆论危机。公众的反应不断推动媒体的报道与政府的回应速度与回应可信性进程。
爆炸案发生两个月后,媒体密切关注事件处理的坚持,表示“唯有追问才能真相大白”。李克强总理也曾在9月21日天津大爆炸事件进展回报上做出“血不能白流、代价不能白付,要将问责进行到底。”的表态。检查专案调查组对在审批、管理和监督等环节存在严重失职渎职问题的相关负责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移交法院依法处理。对当地居民的安抚处理、安居修缮处理此时接近尾声,但将灾后地规划建设“海港生态公园”,被媒体、公众质疑有可能造成二次污染,治标不治本。另外,据中国之声报道,事件发生的二十天内当地收到不少捐款,天津市社会团体管理局及时公示了信息,这些捐赠款物的使用也做到了信息公开。
三、公共危机事件中政府、媒体、公众角色研究
(一)政府角色
首先要明确的是在公共危机沟通的价值取向,应将信息公开确立为公共危机沟通的基本价值取向,将以人为本确立为公共危机沟通的核心价值取向,将社会和谐确立为公共危机沟通的终极价值取向。[5]
在公共危机事件的酝酿期需要政府尽到应急预警机制的制定者的职责,作为公共政策的制定主体之一、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完善政府预警机制能够有效应对突发危机事件,甚至降低危机事件发生的概率。并且《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五条中明确规定:“突发事件应对工作实行预防为主、预防与应急相结合的原则。”。在“8.12”这类突发性危机事件的酝酿期不明显,但我认为政府的预防者的角色还是应当发挥其作用,定期排查安全隐患,尤其是对危险品的存放制定更为严格的要求,或者对当前风险情况进行细致、周全、负责的评估,避免概论疏忽、结果疏忽、统计疏忽、应对方案疏忽、外部风险疏忽,[6]例如汶川地震之前如果能更好地宣传四川处于活动断层的地震知识,可能提高当地建筑标准,可以很大程度上降低此类事件的发生或减少其损害后果。
我国的预警机制不健全主要体现在缺乏足够的灾害应急准备。对危机管理而言,获取信息、相互协调、沟通的基础条件就是对突发事件实行实时监控。2013年的四川雅安地震、2014年的云南景谷地震,我国的地震预警都没有发挥好作用,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7]
到了危机事件的爆发期、扩散期和处理期,政府应当充当危机事件的解决者,由于政府的特殊地位,拥有着强大的组织协调和干预能力,以及无与伦比的社会资源,使得政府在公共危机处理过程中占据绝对的主体地位,发挥着主导作用,应当履行好社会管理职能。其中,在爆发初期及时做出反应至关重要,决定了危机事件的走向。在危机处理阶段,政府要做的绝不是尽快开新闻发布,因为前期调查还没有结束,事故发生原因尚未明晰,这个时候的政府很难给出令人满意的答复。政府需要明白此时应该先做好解决者的本分工作,随后及时公开处理情况,而不是同“8.12”事件中使用“无可奉告”之类的托辞。
危机事件发展到最后的处理结果和后遗症期时,政府应当做好危机事件的总结工作和公众的情绪安抚。政府内部的总结不止于如何做好危机的收尾工作,还要找出事件发生时处理不当的地方以及如何完善,总结该次危机应对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健全危机应对机制,对危机尚存缺陷的方面进行及时弥补和更新,强化各层级官员的行政责任意识。
突发危机事件处理不当很有可能出现政府信任受损的后遗症,当政府信任受损之后,社会公众可能终止与政府积极的互动(如合作、执行政府的政策等),甚至产生消极的互动(如反面预期、游行、示威等),公众不会配合、甚至抵制政府的公共政策,且这种情况可能一直持续到政府采取有效的修复措施。这些负面行为对政府的公共管理产生挑战,因此必须采取措施将政府信任调整回积极的状态。[8]
(二)媒体角色
1948年,美国社会学家、传播学先驱哈罗德·拉斯韦尔在《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中归纳了传媒的三种社会功能,即“环境监视功能”、“社会协调功能”和“社会遗产传承功能”。传媒作为政府和公众之间的桥梁,在公共危机事件的四个时期都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并且新媒体的迅速发展让媒体的发声渠道更加多元化,影响力也在攀升。
由于公共危机事件酝酿期基本不存在,媒体在其他公共危机事件中的敏锐预警者作用难以发挥。在爆发期,这时候的媒体需要发挥作为公众知情权捍卫者和公共危机管理协力者的作用。由于爆发初期,信息的不对称让公众很容易陷入恐慌之中,知情权亟需保障。媒体可以将公共危机信息直接传递给公众,减少信息传递环节,避免信息失真的概率,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谣言和小道消息的产生或终止谣言和小道消息的传播,帮助政府传递信息,协助政府进行公共危机预防、反应和恢复。[9]在2011年温州“抢盐”风波中《温州日报》及时发现并且运用大幅版面报道众生百态,也组织发布击碎“谣盐”的专家文章,充分发挥了协力者作用。
当事件发展到扩散期时,媒体一方面充当政府政策的宣传者,既然危机事件已经产生广泛影响,那么媒体就需要宣传政府有关部门的应急措施,给公众打一剂强心针,为后续事件解决打好基础。另一方面,媒体还需要成为舆情的收集传递者,政府的信息在经过层级传递后,难免发生信息失真、滞后的情况,而处在第一线的媒体能够直观地还原现实。最后的处理期和处理结果和后遗症期,媒体则要推动真相的还原,不断更新危机事件的最新状态,同时能够究其根源,让政府和公众都能从危机事件中汲取经验教训,而不是只在风口浪尖上集中报道,要充分发挥媒体的监督功能。
在后四个时期媒体还有一个共同的角色定位——排气孔和安全阀。媒体关于突发性危机事件中正面或负面的报道都可以排解公众或消极或愤懑或悲伤的情绪,不至于让社会负面情绪的挤压威胁社会稳定,媒体应当成为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所言的社会的“安全阀”。
(三)公众角色
绝大部分公众是不能预知到公共危机事件的,尤其是突发性公共危机时间内,公众能做的就是在危机事件未发生时做好应急知识的学习者,对政府制定的应急方案有一定的了解,汲取媒体传播的预警防护知识,提高自我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参与仿真演练。
在社会面临突发性重大危机时,人的首要需求应是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这两个较低层次的需求。人们一般更喜欢一个安全、可以预料、有组织、有纪律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他所可以依赖的,甚至认为几乎一切都不如安全需要。[10]那么,公众在危机事件爆发时,意识到自己的生命、生存环境受到威胁时,自然就会变成迫切需要信息的接受者,强烈对信息的需求促使公众从最初的不知所措心理恐慌为参与到积极信息传播过程中,尤其是在前四个时期,公众渴望从各种渠道获得信息,追求确定性,同时也不自觉地成为危机信息的传播者,比如“8.12”事件中公众是最早传播相关情况的主体。另一方面,自媒体受众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信息,同时通过媒介发表自己的看法,反馈的速度快到甚至能打乱拉斯韦尔的“5W”传播过程模式。
公共危机事件进入扩散期时,公众就转变成参与者和推动者,一旦事件影响蔓延开来,公众对主体部门应对措施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事件能否尽快解决。在“8.12”事件中公众通过微博、微信平台表达自己的诉求与观点,对政府的回应表示不满反过来迫使政府提供有效信息。这也是公众的权利意识加强,社会参与感提高的表现。
最后的处理期和处理结果和后遗症期,公众更多的是以评价监督者的角色出现。公众作为事件的参与者,他们的意见和评价自然很有价值,通过媒体进行汇总,形成舆情,为政府完善公共危机事件应对策略提供参考。同时,公众能够直观看到事件的后续处理,监督权也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发挥好监督的权利也能促进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
四、政府、媒体、公众互动关系构建
为了能够在实际中更好地扮演各自的角色,政府、媒体和公众应当保持良好的互动、沟通关系。政府与媒体间既相互联系、影响。在危机事件的任何时期,政府都需要媒体为其传递相关讯息,无论预警机制的宣传还是危机信息发布及舆论引导都离不开媒体。这也是“8.12”事件中相关部门紧急召开发布会的原因。也就是说,媒体能够对政府能否尽快解决公共危机事件、是否将危机对社会、公众的影响降到最低起着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在公共危机事件上媒体是否能够及时报道相关信息(从政府方面获取)以及如何报道对其塑造自身形象也有很大影响。当然,媒体对政府还有监督的作用,对于“8.12”事件的处理方式及后续结果,媒体都是密切关注的,并且呼吁对类似的危险品储存严格审查。
就公众层面来讲,与媒体存在着代理关系;对媒体而言,与公众有着信息交换关系。虽然自媒体时代公众也可以发挥媒体的一部分作用,但是主流媒体的影响力远超个人,公众需要媒体的发声。另一方面,政府与公众存在着监督与被监督关系以及合作关系。“众人拾柴火焰高”,光凭政府处理危机事件的效率有限,在专业性要求不高的工作上,公众的参与能够加快危机事件的解决速度。同时,公众也能更好地监督政府工作,减少谣言的产生。
总之,在公共危机事件的酝酿时期政府能够做好预警者,媒体能够为政府的相关政策措施进行宣传,公众能够认真学习;爆发期、扩散期政府能够及时妥善处理,媒体能够在宣传政府解决方案时传递公众的意见,监督政府工作,给公众发泄的渠道,公众理性发声,帮助政府解决问题;处理期和后遗症政府与媒体及时公布进程,做好安抚工作,尽快恢复公众对其的信任,媒体与公众监督政府工作同时给出评价,以便政府总结工作经验与不足。
参考文献:
[1]张海波,童星.中国应急管理结构变化及其理论概化[J].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03期:62.
[2]丁迈,罗佳.心理应激影响下公共危机事件的公众舆论流变——以“昆明暴恐”事件为例[J].现代传播,2015年第2期:50.
[3]斯蒂芬·芬克.危机管理[M].湖南:湖南文艺出版社,2008.
[4]周榕,张德胜.论我国媒体在公共危机事件中的“中间角色”[J].传媒观察,2014年05期:20.
[5]陈世瑞.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沟通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91-94.
[6]霍华德·昆鲁斯,迈克尔·尤西姆等.灾难的启示:建立有效的应急反应战略[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6:75-85.
[7]申振东,郭勇,张罗娜.关于我国公共危机管理的思考——基于近三年60起典型突发事件的分析[J].贵州社会科学,2016年6月第6期:73.
[8]徐彪.公共危机事件后的政府信任修复[J].中国行政管理,2013年第2期:32.
[9]叶春涛.突发公共危机事件处置中地方政府与媒体的角色扮演[J].社科纵横,2013年11期:62.
[10]马斯洛.动机与人格[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上一篇:
返回列表
] [下一篇:
电力系统继电保护新技术的发展与分析
]
相关链接
- 我国农民生活质量发生前所未有的飞跃[2022-05-28]
-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高峰论坛,在杭州举行[2022-05-21]
- 陕西省子长市新一轮退耕还林的现状与建议[2021-01-07]
- 努力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2020-01-17]
- 建设网络强国——习近平一直“在线”[2019-03-25]
-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2019-03-21]
- 新时代推进教育现代化的新征程开启[2019-02-27]
- 深刻体悟和自觉践行伟大改革开放精神[2019-02-13]
- 中国文化的大传统与小传统关系的哲学辨析[2019-01-30]
- 如何理解“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2019-0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