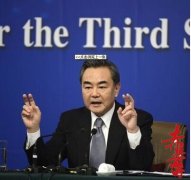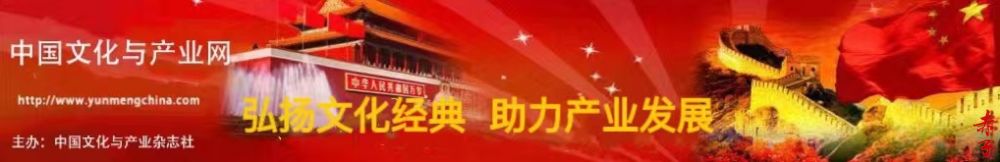

来源: 南方人物周刊 发布时间:2019-03-25
浏览次数: 1693在张经纬这部面向公众的极简史里,我也找到了不少有别于主流史学和考古学的观点。
譬如,在占主流的考古学研究里,从墓葬出土的史前玉器、商周时代的青铜器一直被视作具有形而上色彩的“礼器”——那是宗教祭祀、王权和国家制度的重要象征。
但在张经纬的笔下,这些玉璧、鼎、钟“降格”为更有实际功用的物件——它们是一种“硬通货”,主要用于交换、购买重要物资譬如战马等,以及在战争中用以贿赂别国,也是留给子孙后代的一笔真真实实的财富。
张经纬认为,要把这些从商周时期古墓里出土的玉器、青铜重器,包括“九鼎八簋”,还原到原本的墓葬环境里来认识。
“如果我们用一种古今同理同心的认识来看,就很明显——那就是墓葬环境下给出的一种纪念方式,这些玉器、青铜器是一种冥器,就像汉唐宋元贵族古墓里有大量金银财宝随葬一样。我们不应该以这些冥器的摆放,来想象商周人的日常生活场景。”
据《左传》记载:春秋时期,楚成王想让身为周王室之后的郑国国君对他服服帖帖的,就采取了送礼行贿的方法。“这个礼,不是送大鼎,而是直接送了一千斤铜料。郑国人收到后很高兴,后来就拿它们铸造了几套钟。”
“我还能举出很多这样的例子。”张经纬将之归结为人类学训练带给他的视野——历史中真正重要的,是人们的日常生活;日常生活中真正重要的,是饮食、睡觉、穿衣这些东西,“而不是那些抽象的制度、礼教和儒学道德思想”。
采访中,这位年轻的人类学者也“吐槽”了诸多权威学术观点,包括“秦人东来说”,某些出土古简的可采信度,以及走出“疑古时代”的思潮。
“你要相信自己的生活经验和直觉,无论面对的是多大的学术权威,除非他真能拿出实质性的、压倒性的证据来推翻你原有的观点。”
一个人类学家的日常:捉虫子,在路上
在上海博物馆,张经纬所在的部门是“古代工艺研究部”——主要负责“少数民族工艺馆”的维护,以及藏品的收集、研究和布展。
“其实,主要的工作是捉虫子。”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解释说。博物馆有一整套的工作操作流程。安保人员在巡馆时,如果发现毛皮、织物或饰品表面出现了异样物,就轮到张经纬登场了——他取样,鉴别这些异样物到底是虫卵、霉斑还是其他有机或无机渗出物;然后再把有问题的藏品送到馆里的文物保护和科技实验室做进一步的处理。
2009年春暖花开的季节,上博的“少数民族工艺馆”发生了一起引起数周“骚乱”的毛织物生虫事件。此时正值张经纬被招进上博做馆员,因为时间线如此吻合,同事们都打趣——怀疑是他偷偷把虫子放进博物馆的。
博物馆的工作给张经纬提供了一份稳定的职业和薪水,和相对自由的时间安排。对付完馆里工作,他把余下的时间和精力全部投入到自己的田野调查课题和写作上。
2018年3月,张经纬耗时四年完成的《四夷居中国:东亚大陆人类简史》一书最终出版面世。这是他个人的第一部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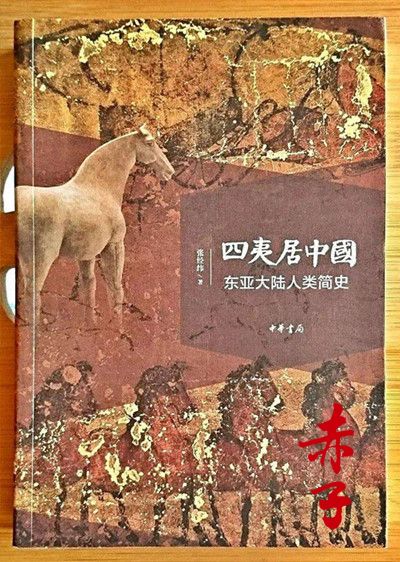
这是一部野心很大的历史人类学作品。它立足于地理历史学,以历史文献、考古发现结合田野考察,试图还原出东亚大陆上不同文化族群从史前到晚近长达万年的迁移史,并尝试解释这背后的趋势和动力,提出了“齿轮模型”说。
研究的思考萌发于他读人类学研究生阶段。在厦门大学,张经纬的论文课题是关于闽、粤等地客家人的迁移史。自那时起,他“很死心眼”地一路向上溯源,追溯到唐代之前的中原和东亚,他的研究对象也由此扩展到整个东亚地区的人类迁移史。
为了完成这本雄心勃勃的著作,张经纬自2010年起花四年间进行了17次地理路线调查,跑遍了除台湾、海南以外的中国全境。
他先从上海坐飞机抵达一个目的地,然后从那里出发,搭乘县与县之间的短途客运大巴,沿着老国道和乡间老路行走,没有公交可坐时就包车考察路线。
“刚开始坐跨省的大巴,后来发现不行。现在修的高速公路裁弯取直,很多地方都是走隧道、高架桥。古代没有隧道,走的都是盘山小路。”
他通常早上6点从A县出发,坐五六个小时到B县。到B县后,午饭也来不及吃,就开始搜索遗留下来的古道和古迹。结束后再坐下一程大巴赶去C县,如果C县的考察能在4点左右结束,那他再买票坐班车赶去D县。到D县,一般已经是晚上八九点了。
“就这样一个县一个县地跑,这跟走高速公路不同,因为过去修的老路是根据当地的地形、地势修的,和古道很接近甚至重合。这种老路给我很大启发,特别是在走乡和乡之间的老路时。”
在路上时,他感觉自己就是电子游戏里那个跑通关的小人,当接近古人的路线时,空中就会掉“金币”下来——可能是一条古道,一段遗址,甚至是当地在旧址上重修的旅游景点。当金币掉得特别快时,他知道自己是听到古人的脚步声了。
2011年,他从宁夏出发,在陕西穿过秦岭到达商洛至商南时,他抬头看到国道的山门牌楼上赫然写着“雄秦秀楚”四个大字。他感觉自己被一个大金币砸中了——“那里是古代秦国和楚国的分界地带,过去曾设界碑石,标明那里是从秦到楚的必经之路。”
这些田野调查所需的费用,都由张经纬自己承担。
博物馆的薪水有限。为了筹措田野调查所需的盘缠,他靠业余时间码字赚稿费,从最早翻译西方学术著作,到为媒体撰写书评、专栏文章,到如今赶上这一趟新媒体和知识付费的班车。
在最紧张的巅峰时期,张经纬保持着周一到周五写自己的书稿,周末两天集中为媒体写约稿的频率。
这种面向大众媒体的高强度写作生活,也训练了他的写作技巧和文风——通俗,诙谐,擅长以故事切入话题。“用几千字集中把一个点说透、说清楚”,“尽量不让自己做书呆子。”
未来20年,这位雄心勃勃的青年人类学家已经为自己挖好了一排“坑”——在已有的研究框架和理论模型上继续深入、拓展、细化。他的两部学术类书稿正在写作中,一本将在“齿轮模型”上继续探讨人类史,另一本则将探索中国古人的精神世界和文化观念的形成。
“所以,我很感谢合作过的编辑一直约我写书评、给我发稿费,支持我的研究。”这位刚刚在万年时空里谈笑纵横的人类学家瞬间落到了地面上,真诚地致谢起来。
责编:谢青青(电话:010—65420087 邮箱:chizizzs@163.com)
相关链接
-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省总林长:张庆伟主持召开2022年省总林长会议[2022-06-18]
- 把公平正义落实到每一起案件中——访党的十八大、十九大代表陈燕萍[2022-06-18]
- 党代表丨迟妍妍: 将黑龙江农产品销往全国各地[2022-05-03]
- 全国人大代表陈春芳:党支部领办合作社 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2022-03-09]
- 全国人大代表倪海琼:建议美丽乡村推广应用超低能耗建筑[2022-03-07]
- 全国政协委员武义青:协同发展 建设先进制造业集群时不我待[2022-03-06]
- 戚发轫:助推航天强国梦 漫步寰宇度春秋[2020-01-16]
- 任何人都阻挡不了中国航天的崛起 ——访中国著名空间技术专家戚发轫院士[2020-01-06]
- 蔡名照:智库对“一带一路”广泛研究成重要文化现象[2019-05-09]
- 张经纬 博物馆里的“网红”人类学家(续)[2019-03-25]